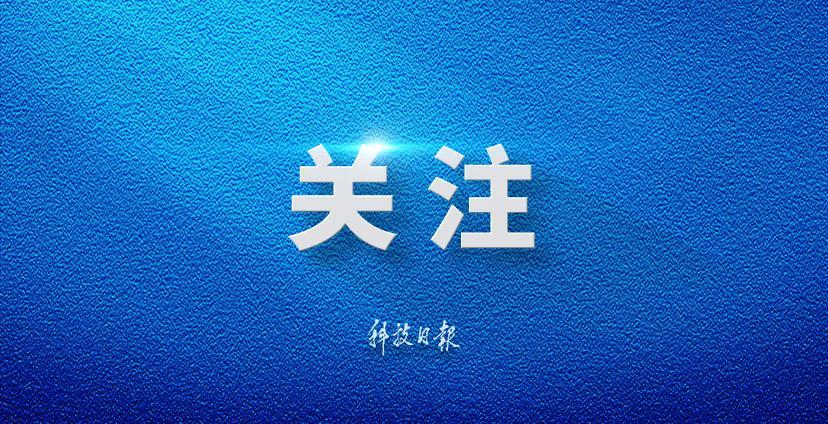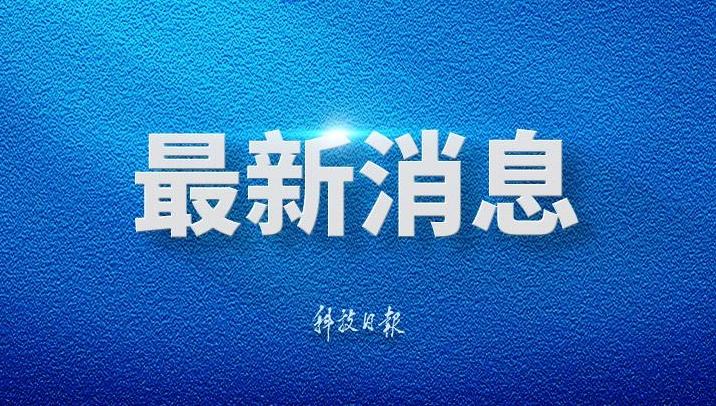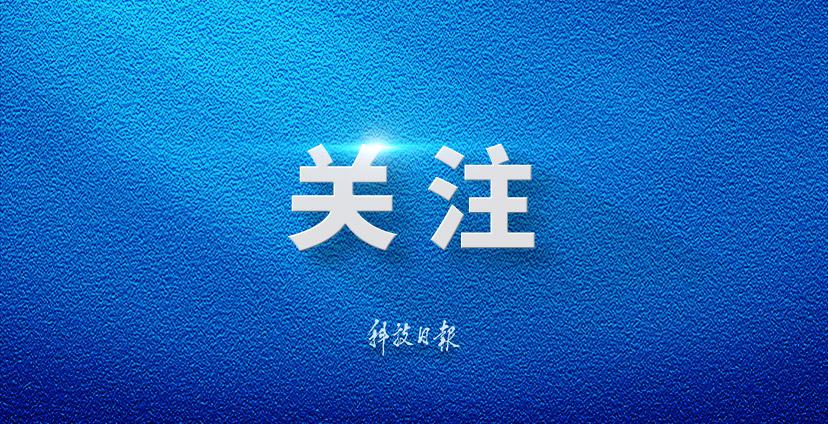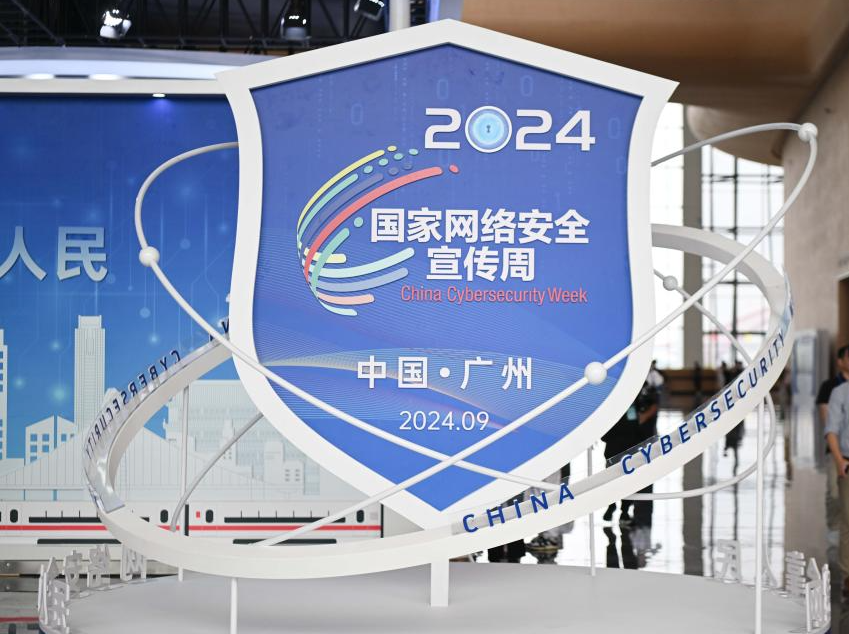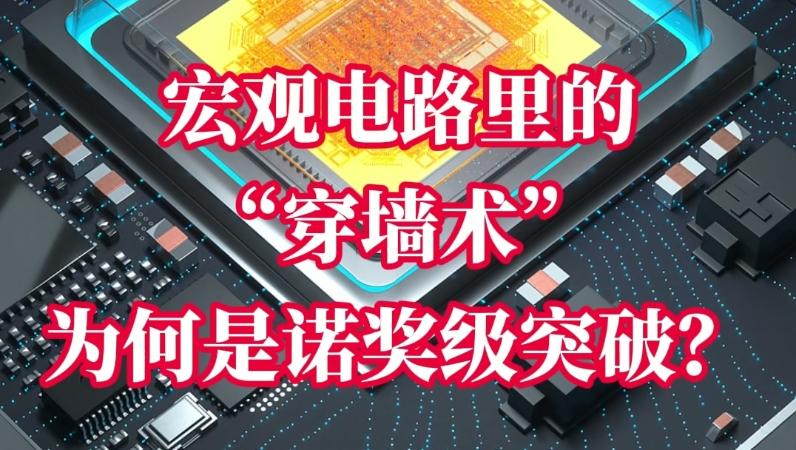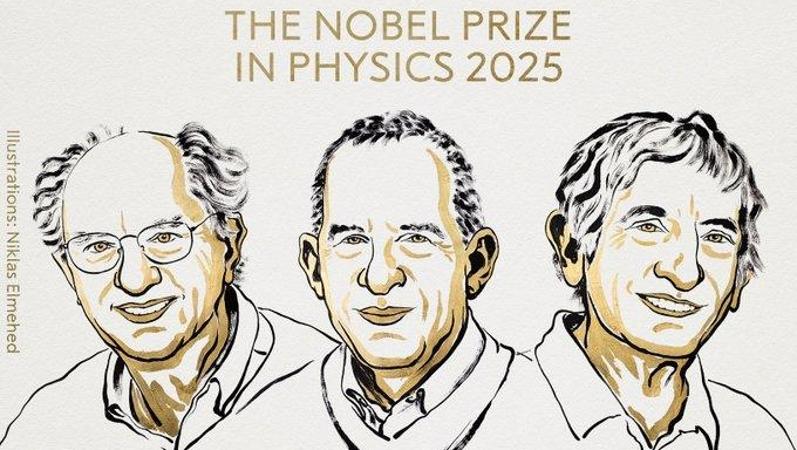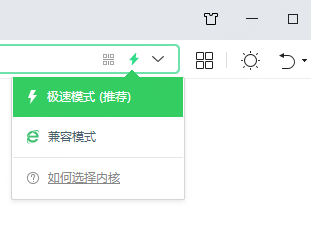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观点聚焦
主持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物种起源》,是我又一次与达尔文结缘。
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由我们团队重新翻译的《物种起源》,近年来先后推出了红皮经典版、彩图珍藏版、学生版和学科版共四个版本。
它的语言文字更加现代化,书中还有我撰写的长篇导读,能帮助青少年快速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我也如实告诉读者,达尔文进化论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留下一些难题,我希望能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启发后来者继续深入探索,推动进化论不断发展。
《物种起源》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伟大遗产,是经典中的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现在和今后它仍然是指引人们前进的灯塔。它的核心思想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自然选择原理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还广泛适用于物理、化学和地球科学,甚至对社会人文科学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达尔文创立的“生命谱系树”思想现在被分子生物学证实,并广泛应用于现代生命科学的各个分支,甚至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刑侦破案。
——舒德干
不久前,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教授舒德干手中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一枚纪念币。
纪念币的一面是“第一动物树”,另一面是“天下第一鱼”。这些都是舒德干团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几十年来,舒德干扑在古生物学研究上,致力于破解达尔文留下的谜题,为揭示地球生命演化过程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近些年,他又在科普上费了许多力气,努力用“接地气”的方式为大众介绍古生物学。
在专访中,舒德干分享了他的科研经历和科研理念,反复强调理性质疑精神的重要性。舒德干说,达尔文留下的,不仅是进化论,还有坚持、探索和不畏权威的思想光辉。

破解达尔文留下的谜题
记者:您在今年北京大学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上说,您一直不忘初心,循着达尔文的足迹前行。能否向我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舒德干:1964年,我从湖北黄冈中学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受高中生物老师的启发,我选择了古生物学专业。这一领域是进化科学的实证殿堂,在这个专业开展学习、研究,极富挑战性。
北京大学一直鼓励学生强基础、宽口径学习;希望培育思想自由,能够在学科交叉领域实现学术创新的学生。因此,生物专业不仅给我们开设了多门生物基础课,还特别开设了能激发我们“质疑思维”的达尔文主义课。达尔文改变人类自然观和世界观的科学进化论为我们带来了思想启蒙。在课堂讨论中,我们也为他在《物种起源》中留下的世纪谜题争论得面红耳赤,都立志日后要用化石实证破解这些难题,发展进化论。
我之后的工作可以概括为这几个字——循着达尔文的足迹前行。我在达尔文留下的几个主要谜题的破解方面获得了实质性突破。
记者:您送给我的纪念币上的“第一动物树”和“天下第一鱼”,是不是就是这些突破的一部分?
舒德干:俗称“寒武纪大爆发”的奇特现象至今仍是进化生物学的一大悬案,主张渐变论的达尔文坚持认为“自然界不存在飞跃”,但随着大化石记录越来越多,“动物大爆发”的景观越来越清晰。
我们综合分析早期生命化石大数据,提出“三幕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假说,认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分三幕依次创生了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后口动物三个亚界齐全的“第一动物树”。在约5.7亿—5.4亿年前,诞生了早期基础动物亚界,接着在寒武纪初期的5.4亿—5.2亿年前,爆发式创造了原口动物亚界中的大多数主要门类,在5.2亿—5.18亿年前的澄江动物群期间,快速创造了后口动物亚界中的所有门类。
达尔文论证出“人类由低等动物逐步演进而来”,但是人类远祖是如何缔造出一系列基础器官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团队历时十余年,先后发现动物界早期的华夏鳗、长江海鞘等低等脊索动物,以及脊椎动物“昆明鱼目”,并创立了古虫动物门。我们初步揭示了人类远祖近亲们陆续创造出一系列基础器官,从而实现呼吸系统革命、运动系统革新和神经系统大升级的证据。
这里重点说一下“天下第一鱼”,即昆明鱼。1999年,我们发现了昆明鱼,它将世界上最早的鱼的纪录向前推进了5000万年,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鱼”。它也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原始脊椎动物,首创了原始脊椎骨。正是原始脊椎骨的产生,才使得今天人类的直立行走成为可能。同时,昆明鱼首创了具有原始形态的眼睛和大脑,智人大脑聪慧无比,更应该感恩这条“天下第一鱼”“从0到1”的首创。
记者:现在古生物学领域,还有哪些有待后人解决的难题?
舒德干:一定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脊椎动物有八大系统,我们比较好地发现了四种系统,即呼吸系统、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化石起源证据。但还有一些系统的起源证据,我们在化石里仍没有找到。
因此,研究者们还需要继续做野外发掘工作,寻找更多化石;同时要善于用新的技术手段,更精细地研究化石构造,以此找到剩余系统的化石起源证据。
我国的澄江化石群是一大宝库,它保留了软躯体的化石信息,世间罕有。在这个地方,依然有可能产生更多世界级的发现。
年轻人不要做“小绵羊”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起,您和团队就已经在“啃”世界前沿的大问题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那么“敢想”?
舒德干:我之所以有些“敢想”,与我的偶像达尔文有关。在上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我就体会到,在进化古生物学领域,要想有所成就,有一条捷径,就是按照灯塔“指引”的方向走。
达尔文思考了很多大问题,敢于挑战世界前沿难题:物种是否可变,如何起源?他就是一个非常“敢想”的人。他的科学质疑精神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在那个宗教一统天下的年代,他连“神创论”都敢怀疑。而且他不是盲目怀疑。达尔文有知识积累,他不仅从科学和逻辑上推论物种如何起源,也到自然界中去收集证据。
我们做研究也是这样。研究古生物学,要先有相关的理论知识积累,再去找野外的化石证据。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啃”那些大问题时,我就觉得,能在澄江动物群化石宝库中工作,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化石宝库中取得一些重大发现,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遇。如果不“敢想”,就根本不可能有新发现,也就不能产生新思想。
我保持好奇心,不断激发自身的科学想象力,聚焦大问题,寻求思想理论创新,在古生物学领域一干就是35年。其间我在学术上也犯过错误,遭遇过挫折,这些提醒我要更加严谨求实,继续攀登。
记者:您多次提到理性质疑精神,这种精神为什么重要?
舒德干:要是没有质疑精神,就做不了科学研究。你都不敢去怀疑前人书本上的东西,那就很难去做有大创新的事情。我认为,理性质疑这个理念必须植根在青少年的心中,他们要把自己的直接经验和从书本上学到的间接经验勾连在一起,也就是将实践和理论勾连在一起,这样才能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想法。
我们也要鼓励年轻人“敢想”,就算这个想法只有30%的道理,也要允许他们提出、讨论。
我也鼓励年轻人有点反叛精神,不要做“小绵羊”。我从小就不太听老师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能不能做一些跟前人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万一做对了,那就是个创新;做错了,我是个青年人嘛,也没有关系。
记者:您花了很多精力做科普,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在科普中培养这种理性质疑的精神?
舒德干:对,我鼓励青少年有自己的想法。在线下做讲座时,每次都会有提问和交流时间,我就说你们要多批评舒老师,我哪些地方讲得不对,都可以指出来。
我觉得做科普,要引起科普对象的兴趣,让他们产生好奇心。连好奇心都没有,何谈质疑。只有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是这样,才可能去质疑。如果你完全相信专家、相信老师,就很难有创新。
我总跟科普对象们说,不要觉得舒老师是院士,就说的什么都对。院士只是在他自己那个行当里懂得稍微多一点,好多其他地方都是外行。
将知识财富还给大众
记者:对于做科普,您有哪些心得体会?您曾说要做“高级科普”,什么叫“高级科普”?
舒德干:科普非常重要,尤其对于提高全民族科学素养至关重要。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和奉献,我们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很难创造物质财富,但可以创造知识等精神财富,而且有责任将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还给大众。科普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为了做好科普,我的确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也享受到了其中的快乐。
“高级科普”主要指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涉及重要科学发现的科普,比如传播进化思想和规律,重大进化事件。做好高质量科普很难,需要把问题吃透,学习怎么把高深的学术话题用接地气的语言告诉大众,PPT也要下功夫去做。
记者: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了解古生物学?
舒德干:古生物学的本质是生物演化的历史科学。地球上有两门历史,一门是我们熟悉的人文社会的历史;另一门,则是关于地球生命40亿年演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我们人类至少5亿多年的起源进化史。
了解生物演化史,除了获得一些实用价值外,还能使我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如果作为一个人,都不知道人类演化的历史,那就太没意思了,好像精神上缺了一大块。而且,如果你能了解人类的演化史,你就会觉得,做人还是很幸运的,人还是很伟大的。
而且,我们要用科学思维来认识人类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演化规律。我做科普时发现,很多人还没听说过人是从鱼演化来的,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在国外,由于受到宗教信仰影响,“神创论”更是大行其道。古生物学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需要严谨的实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唯物主义是它的核心灵魂。了解古生物学,对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探索方法也十分有益。
记者:现在人工智能(AI)发展迅速,您认为AI对古生物学能起到什么作用?
舒德干:AI作为现代的一种高效技术手段,已经应用于多种科学研究中,比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它无疑也能促进古生物学的发展。目前AI已经开始成功应用于化石的快速鉴定和分类,以及图片和立体图像分析,比如脊椎动物骨骼建模等。今后其应用将逐步深入到生物演化和生态环境重建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为了在研究中用好AI,我们应该注重从两个方面同时打好基础,一是懂AI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二是全面而准确地掌握相关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知识。
年轻人要学会用AI,用它来帮助自己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学AI,现在做研究就可能比别人慢半拍,以后会慢一拍,最后就可能会慢十拍,导致别人能做的事情做不了或者做不快。
记者:古生物学专业现在看来依然是一个冷门小众专业,您怎么看待古生物学的冷和热?
舒德干:我觉得现在好像古生物学在慢慢变热。一方面随着大家科学素养的提高,更多人知道了这门学科的意义;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做得也比较像样了,在国际上也已经很能站得住脚了。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像徐星、周忠和、朱敏等一批人都做得非常棒,他们也做了很多科普工作,让更多人知道了古生物学。
记者:如果有人想学古生物学,您想对他说什么?
舒德干:我想说太欢迎了,你们今后一定有前途,一定能够享受这一门学科。希望你们保持对古生物学的热爱,享受探索未知带来的快乐。
学古生物学的目的,不仅是给自己谋一个饭碗。中国在生物进化几个关键时段都有很丰富的化石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它们破译更多演化密码。
我们已经是过去的一代,新的一代有更扎实的理论基础,有更强烈的质疑精神,还有AI这样强大的工具做辅助。我相信长江后浪一定会超过前浪。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